曾皙之志的礼意、乐意和诗意
郑坛建
大多数关于《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(下称《侍坐》)的解释,都比较关注曾皙“所言之志”,却或多或少地忽略“如何言志”,即曾皙言志的具体方式和具体过程。《侍坐》作为《论语·先进》的最后一章,不仅篇幅长,人物多,而且叙事中突出了戏剧性,犹如柏拉图的“哲学戏剧”。对于这样的文本,只有透过形式分析,关注叙事手法和语言技巧,才可能有深入的理解。孔子欣赏曾皙,不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人生理想,而是因为他以一种充满音乐意味的形式和音乐性的语言——诗,描绘了与自然时令合拍的生命状态,这种生命状态在孔子看来内在包含着礼乐的目的和结果,即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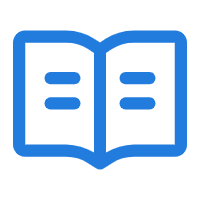 在线阅读
在线阅读
 全文下载
全文下载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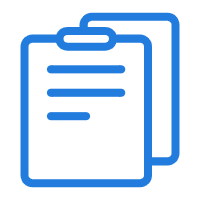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赣公网安备 36012102000372号
赣公网安备 36012102000372号
 互知学术
互知学术
 全科互知
全科互知